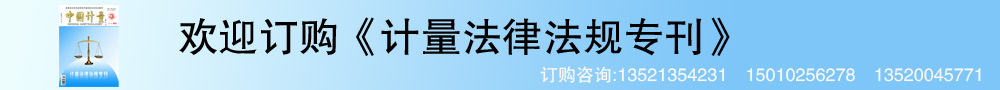
我1955年从北京机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计量检定所。当时的计量所筹建不久,而且还在建设,但却开展了不少业务工作。技术工作主要由长度(计量)组和热力(计量)组承担。热力组分成热工(计量)和力学(计量)两个部分,力学是搞测力硬度,而热工开展的工作基本上是温度计量,且主要是高温部分。无论是测力硬度还是高温计量都是一机部所属企业亟待开展和加强的工作。“热工”下面又分为两摊,一是(计量)监督(以下简称监督组),另一是(计量)检定(以下简称检定组)。我一开始就分配搞监督,这是我走出校门参加工作所接触的第一项技术业务。
当时计量工作的方针概括为八个字:“准确一致 正确使用”,简称为计量工作八字方针。一机部的计量工作都贯彻这个方针,监督组当然也不例外。具体任务是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其中了解一机部重点企业温度计量工作情况是主要内容,特别是在开始阶段,它包括:加热设备的名称、型号、工艺温度及准确度要求;计量仪器的类别、数量及使用;机构或人员的配置(包括人员的文化水平、从事温度计量的资历);规章制度等。对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能解决的就地解决,不能解决的带回单位综合考虑。建议的提出,属于具体技术问题一般向仪器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直接提出,对于诸如方针政策,机构、人员、仪器设备的配置,经费等大的方面要和厂领导面谈。当时强调要尽可能地争取技术副厂长或总工程师的接见,以引起厂里的重视。当时工厂乃至整个社会对于计量认识不足、甚至知之甚少,与厂领导面谈主要目的是宣传计量工作的重要性,计量与生产的关系,以取得厂里的重视和支持,当时下厂的介绍信都是从一机部开出,也有这种考虑(表明是代表部进行监督性调查)吧!监督组的人员全部是1954—1956年从一机部所属机校毕业的学生,这些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和厂领导谈话开始还真有点怵头,不得不作一些精心准备,硬着头皮上阵。好在厂领导们工作再忙也会抽时间接见,并以礼相待,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汇总、研究、总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调研,为以后的计量工作开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如人员的培训、资料的译编以及检定组研制二等标准铂铑10—铂热电偶,请苏联专家协助、指导工作等。
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工作的方式方法,监督组的下厂时间相当多,因此,我参加工作一年多时间两次出差东北、一次中南、西南地区。当时一机部所属工厂都在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开始阶段都是两人一组分赴这几个地区。
我第一次去东北是随高佩珍同志一起、由她负责。 1955年9月18日登上旅程,这时距我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仅有40天。因为所学的金属切削专业与所要搞的热工计量相差甚远,所以此行说是工作、实际是学习,跟老同志学习,通过实践学习。此次东北之行共去沈阳、抚顺、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5个城市,12个厂,其路线是:北京→(经沈阳)抚顺→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重返)哈尔滨→长春→北京。12个厂是:抚顺重型机器厂; 沈阳 变压器厂、风动工具厂;哈尔滨 电机厂、电池厂、工具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齐齐哈尔 机车车辆厂、第一机床厂;长春 第一汽车制造厂(代号652)。从9月18日启程到10月24日回京总计36天。
我们所去的这些工厂大都有参加一机部计量检定所举办的上海训练班学习的学员,所以一般是先找学员,然后去他们所属的部门。厂里的热工计量不像长度计量那样,有统一的专门机构负责(一般是在检查(验)科下设有计量室),而是由一个或多个部门代管或分管,其中有实验室、化验室、中心实验室、检查科、设备科,也有少数是由以上部门与车间分管,职能部门管“检定”;车间管仪表和使用。像当时‘652’那样有专职部门(仪表车间)管理的只是极个别厂。到厂以后,分管热工计量的部门领导会作一般的介绍,主要还是学员进行全面具体的介绍,然后去车间(最主要的是热处理车间,有的厂还有铸造、铸钢及锻造车间,)和化验室了解仪器、设备及安装使用等情况,这些都要作详细记录。在此基础上再和部门领导谈我们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并征求对我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当时我国的热工计量真是薄弱,存在的问题和需求相当多,尽管我们所去的厂基本上都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所用仪器设备来自多个国家,以苏联的为多,此外还有国产的、东德的,甚至还有美国的。没有专门的计量管理和技术机构;缺乏标准仪器(如热电偶、电位差计)和检定用设备,只有少数厂有从苏联进口的;缺少专用和修理用材料、备件(如补偿导线、标准电池);仪器的安装使用不当(如环境恶劣、热电偶参考端温度高且不加修正);大多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急需技术人员的培训和专业知识的普及,这些都是普遍现象,亟待解决。有的提出要求进行人员培训、提供专业技术资料;有的提出统一解决仪器设备问题,特别是标准仪器(当时控制严格,除苏联援建配套的以外,需要补充和增购的、都是苏联专家直接向一机部提出计划)。有两个厂提出标准电池冻坏,652就希望我们向部里反映由苏联进口的标准电池运输中冻坏问题。
在每个厂工作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难的一环是向厂领导汇报和建议,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都很忙。相当多的厂是司局级编制,但当时的厂长没有豪华的办公室,没有高级轿车,没有先进的办公设备,在厂长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的是各种图表、锦旗、响个不停的电话和进进出出、行色匆匆的身影。如果把工厂比作战场,那么厂长办公室就是指挥部,厂长们就是指挥员。要想得到指挥员的接见必须预约、而且常常不止一次,下面一段笔记可见一斑。
“下午去另外一个厂,会见的总工程师是、名字非常熟悉的娄希翱同志。……虽然上班了,他才吃中午饭,而且是边吃边与人谈话。也就是在吃饭当中接见了我们,用不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过3次、打过三次电话才能见面的原因。……”
( 1955年10月18日 于哈尔滨市工作笔记)。
1956年夏秋之际我和邓锡祥同志去中南、西南地区,跨越5个省,去了6个城市、10个厂。路线是:北京→(经武汉)长沙→湘潭→醴陵(邓)南昌(李)→(重返)长沙→广州→(经柳州)贵阳→昆明→(经重庆)→北京。10个厂是:长沙机床厂、湘潭电机厂、湘潭电线厂、醴陵陶瓷厂、南昌柴油机厂、广州造船厂、贵阳矿山机器厂、昆明机床厂、昆明电机厂、昆明电线厂。从八月中旬出发到十月初返回北京总计也是一个多月。
在这两个地区工作的内容、方式和过程与东北基本相同,但由于地区和季节的关系,这次出差还是比较艰苦的,不过也很有意思,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我当时做过一些笔记,可惜后来都已遗失,下面就所能想起的作一些回顾。
八月中正是暑热天,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更是热不可忍,估计温度至少38℃,即使呆着不动也是汗流浃背。所以从北京乘火车抵达后,不敢停留,连夜乘慢车赶赴长沙。临时买的站票,过道里挤满了人,转身都困难,后来从一个小站下车走到卧铺车,还算幸运、搞到两张卧铺票。长沙的热比起武汉毫不逊色,湘潭也是如此。在湘潭、住宿处室温太高,好多人夜间都搬到室外睡,入乡随俗、我们也这样度过了几夜。从湘潭我和老邓分开,他去醴陵,我去南昌,然后在长沙会合同去广州。广州没有传说和想象中那么热,至少比湖南要好多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凉风习习,很是爽快,且无蚊虫之扰,这可能与所住招待所临近江边有关吧!广州工作的结束也是中南地区工作的结束,下一步就是包括云、贵两省的西南地区。
从广州乘轮船逆西江而上,经肇庆至(广西)梧州,再换乘小船沿浔江、郁江至贵县。从贵县乘火车至柳州,转乘慢车至金城江,据说这条铁路还是抗战时期的,再往前走就只能改乘汽车了。休息一夜乘汽车经(贵州)都匀到达贵阳。
初识贵阳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到这里工作,算是预示、也是缘分吧!所以要多写上两笔。贵阳是个内陆城市,虽然是西南地区的枢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但当时交通很不发达,对外联系只有公路。我想可能正是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发达的公路,使得他具有一座非常漂亮而又实用的客车站(长途汽车站),这应当是当时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宽阔的停车场、舒适的候车室,特别是那黄黄绿绿的琉璃瓦,从很远就可看到,真可以和北京地安门外的大屋顶相媲美,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客车站也非常罕见。
当时贵阳市内交通也差,只有几路公交车,我们所要去的矿山机器厂距市内只有17华里,也要在客车站等班车。贵阳矿山机器厂始建于1936年,是一个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企业,也是一机部在西南地区的重点企业,设备虽算不得先进(有的仪表还是解放前美国生产的),却很齐全。最后的工作是汪福清总工程师接见我们,他为人谦和,认真听取了汇报、作了原则表态。说来也很有意思,三十年后我们又有机会会晤,作为省政协副主席的汪总被聘为贵州省计量与仪器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委员,我作为一般委员,所以每年都有机会见面,但对于这三十年前的往事我一直没有提及。
告别贵阳又经过两天旅程到达四季如春的昆明,下榻昆明机床厂招待所。昆明工作结束此次下厂任务基本完成,但‘打道回府’的路上还有一番跋涉。从昆明出发经(贵州)毕节、(四川)叙永、泸州,再到重庆,一路都是乘长途汽车。汽车都是在大山中蜿蜒穿行,路面很窄,有时连会车都难,路况很差,时有颠簸。车子陈旧,乘客超员,过道处要加座位。每天都是天不亮就上路,傍晚到达宿处。记得有一次赶到旅店已是深夜,乡村旅店照明很差,只有两盏油灯。模糊中每人抱一捆稻草,跟着有手电的人爬上一个木屋的顶楼。铺开稻草和衣倒头便睡,好像没好久,天没亮又要赶路。
据锡祥回忆,在大西南的旅途中要经过一个72 拐山(据说盘转72次才翻过此山),当时是夏天,到山顶就犹如冬天一样,又没带冬天衣服,只好跟车下的小贩买些土毛衣穿。有时晚上,还要打着手电筒到处去找旅馆,所谓旅馆只是在地板上打个通铺能睡觉的私人小店而已(也没电,只点一根腊)。我用小书包背着借来2000元的旅差费,白天抱在怀里,晚上当枕头,整天提心吊胆,椐说那里常有土匪。历时近一个月行程千里,最后也只花了3百多元 钱的旅费(但相当我一年的工资了),后来还受到财务处的批评(说借的太多了),但当时又有谁能告诉准确的预算呀?回忆过去往事,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尽艰难险阻,也很有趣。
就这样晓行夜宿直到泸州才算告别那崇山峻岭,9月底到重庆,这一行程共计四天的时间。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经武汉转乘火车,一路顺畅抵京。
第二次去东北好像也是1956年,由金华彰同志负责,张岱明、秦荫堂和我(是否有周嘉龄已记不清)参加。此次下厂的目的除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为搞协作组作准备。由于笔记的遗失,多年的往事记忆中已经模糊。印象深的是沈阳电线厂,这是苏联援建的一个新厂,热工计量完备,机构、规章制度健全,工作和标准仪器设备都是援建配套而来,技术力量也较强,当时是想请他们负责在沈阳搞协作组的。据锡祥回忆,沈阳地区的协作组是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徐海涵任组长,沈阳风动工具厂李月珍任副组长。
就我的印象,热工监督工作到1957年一直在进行,协作组搞的时间还要长。
金华彰同志作为监督组的中坚力量搞了很多工作,比如曾经请长度组李慎安同志给热工监督组做过报告,专门介绍长度计量开展监督工作的经验。后来在上海、天津等地搞的协作组也都很有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计量工作初创的历史,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值得回顾,值得追记!建国初期,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计量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开始关注工业计量工作,从而建立一机部计量检定所。首先开展工业企业急需解决的长度和热工计量工作,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开展计量监督、培训计量人员、建立计量标准、开展检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计量技术问题等工作,这为我国计量工作全面发展所需的必要准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注:此文曾征求金华彰、邓锡祥二同志意见,感谢华彰的修改意见和锡祥的补充回忆。
(注:李培国是1955年参加温度计量工作的老同志,后调贵州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从事温度计量科研技术工作,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40年)计量工作,业务专研,工作认真,还有一定的文学水平,是我们老战友中一名实干家。)
内容推荐
更多>2020-10-09
2019-06-17